多一双筷子的事儿
冰点特稿第1245期
多一双筷子的事儿

11月21日,湖北省老河口市薛集镇陈庙村,陈小峰在自家养鸡场给鸡喂食。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摄

11月16日,湖北省老河口市薛集镇陈庙村,在陈小峰家养鸡场前,从河北省泊头市赶来的亲人见到都红江(中),拥抱痛哭。 老河口市公安局供图

陈小峰给都红江做的“防走丢联络牌”。受访者供图

11月16日,湖北省老河口市薛集镇陈庙村,都红江(右三)与家人、陈小峰(右一)、民警坐在一起。老河口市公安局供图
都红江在一个雾天消失,又在一个雾天归来。
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这位聋哑人当初是如何从河北省去了湖北省,他的一些经历仍是一团迷雾。已知的事实是,2008年10月4日清晨,河北省泊头市四营镇都李泊洛村村民都红江打算去五六里地外的姑妈家。当地盛产鸭梨,他从家门口的梨树摘下一筐梨,绑在自行车后座。吃过早饭,他骑上车,迎着浓雾出发了。
姑妈没能等到这些鸭梨。都红江这个时年40岁的男人,自此消失了。
一年多之后,湖北省老河口市一家电器厂的工人陈小峰下了班,从厂区出来,看到了他。
1
根据陈小峰的回忆,那是2009年年末的一个傍晚,路边一个只穿单衣和拖鞋的男人引起了他的注意。男人看起来四十来岁,背了个编织袋,拖鞋裂了几条口子。白天刚下过雪,雪渍还没干透。
陈小峰问他冷不冷,男人边摇头,边比划。他要去哪里、吃饭没有、有没有地方住?陈小峰打出个“吃饭”的手势,男人使劲儿点头。陈小峰带他来到附近一家小炒摊,点了两份炒饭。男人狼吞虎咽,把自己那份一扫而光。
陈小峰一下子想起10年前,自己也曾这样“吞”过饭。
1999年春节过完,他17岁,第一次离开老河口,去广东省潮州市打工。他本来要去一家工厂,介绍人临时变卦,联系不上了。他就在厂门口傻等。他身上只剩30多元钱,工厂在郊区,附近没商店,他不敢走远去买饭或买水,生怕一挪步就会错过介绍人。连续两天,他饿了就吃点从老家出发时带的、路上没吃完的饼干,渴了就忍着,晚上就在厂门前打地铺。直到厂里一位表叔带他去吃了饭、找了落脚之处。
面对这个狼吞虎咽的流浪汉,陈小峰当时感到很为难。他平时住在工厂宿舍,没有多余的铺位。放手不管,又于心不忍。最后,他让这个陌生人坐到自己摩托车后座上,带回了30公里外薛集镇陈庙村的家里。
那时,陈小峰27岁,孩子5岁,妻子在浙江杭州打工,“一家人负担大得很”。因为不知对方来历,他也不放心,跟厂里请了几天假,决定先在家帮着安顿一下。
他和父母打开了都红江随身携带的编织袋,里面除了脏衣服,其他什么也没有。他们收拾出床铺,找出干净衣服给他,打来热水让他洗澡。都红江接过衣服,但不洗澡也不刷牙。陈小峰决定再观察几天。不知道他的名字,一家人就统一称他“哑巴”。
第二天,他们发现,吃饭时,哑巴只吃面前碗里的菜,从不在盘中抄来抄去。陈小峰的父亲陈丰全给他倒酒,他用双手接过。敬酒时,他总将自己的杯口端得低些。吃完饭,他还帮忙端碗收筷,连续几天如此,也愿意洗澡、刷牙了,“看着是个本分人”。
陈小峰很想知道他是哪里人,怎样可以帮他回家。在这之前,他没有与聋哑人打过交道,只得尝试比划着“问”。哑巴比划不出,被问得多了,举起双手猛拍自己的头部。
担心他大脑可能受过刺激,陈小峰不敢再问。当天,陈小峰找来纸笔,引导他写字。但哑巴只会写“都”“江”“四”“川”4个字。想着2008年四川刚经历大地震,会不会是从都江堰逃难来到这里的?陈小峰去派出所报案,想要查个清楚。户籍民警向市公安局报备,联系四川公安调查,也没能查到有效信息。
陈小峰的父母在家守着一亩多地务农,有时在附近打零工。眼看春节快到了,一家人决定,让哑巴先在家住着,“反正也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儿”。
陈小峰发现,哑巴腿上有几道伤口,已经化脓,有时还用手按着肚子。陈小峰带他去了村卫生室,后来又去镇卫生院住院,治了约莫一个月后痊愈。
医药费花去1000多元,陈小峰结了账。
母亲孙金莲唯一担心的是,邻居们会不会不乐意。
邻居陈丰举记得,刚听说陈家收留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聋哑人,邻居们一度有所防范。他们暗中观察了一段时间,普通的农活儿这人都会做,而且个性随和,不讨人嫌。
“人不坏,还聪明,邻居们平时一起相处,他基本能懂我们的意思。又勤快,他不比一个普通劳力差,帮做很多事。”陈丰举说。
陈小峰这样向大家解释:“他没地方去,又是个哑巴、听不见,先让他跟我们一起住着。”
2
这个陌生人进家第二天,陈丰全就发现,他会喝酒,也抽烟。
陈小峰是烟酒不沾的。回工厂上班前,他把哑巴带到村里小卖部买烟。哑巴拿的是10多元一包的“好烟”,陈小峰月工资2000元,跟他比划“烟可以抽便宜点的”。哑巴就改拿五六元一包的。
陈小峰跟店主交代,如果哑巴来买烟酒,记在他账上。
那年,陈小峰家刚盖起楼房,因为钱不够用,二楼的几间房没有安装房门。过年时,为了多挣些钱、节省开支,他妻子没有回家,在厂里加班。
妻子并不知道哑巴的存在,直到一年后回家,才发现家里“多了个人”。按照陈小峰的说法,“这不是多大的事儿”,况且哑巴没处去、人也不坏,就让他先在家住着,同时继续帮他寻亲。妻子觉得“也有道理”,没有多说什么,继续出门打工。
时间久了,哑巴像生活在自己家一样。周边有人家盖房,他也会去砌砖、提水泥;有人家办红白喜事开流水席,他去灶边烧火。别人给他工钱,他摆手不收,留他吃饭,他也回家吃。
哑巴来的第三年,陈小峰夫妇有了女儿,家里负担更重了。
2015年,周边有村民养殖蛋鸡挣了钱,陈小峰拿出几万元积蓄,找亲戚借了些钱,开起一家养鸡场。养鸡场在离家四五百米的一处荒坡上。他们平整地面、盖起厂房、搭建生产线、赊来饲料与鸡苗,哑巴也一起干。工地夜里得有人守护,陈小峰就在荒坡旁搭间窝棚睡觉,哑巴在旁边陪着。
陈小峰“运气不太好”:鸡长大下蛋了,禽流感来了。这批蛋鸡,赔了20多万元。
养鸡场有5间房,仓库、厨房之外,陈小峰住一间,哑巴住一间。那阵子,陈小峰日夜躺在床上,闭门不出。哑巴做好饭菜,端来热水,陈小峰不吃也不喝。
叔叔来劝他,“这样躺着,欠下的债咋整?你和哑巴两人的开销咋整?”
消沉了一周,陈小峰决定到镇上打零工,每天工钱100元。
即便是最难的时候,陈小峰也没有中断哑巴的烟酒。有时他给哑巴零花钱,哑巴拍拍口袋比划,意思是有钱、不用给。
陈小峰想过,在周边给哑巴找点活儿做。但他没有身份证,与人沟通不便,没人要他。
“光靠打零工还不了外债。”七八个月后,他找银行贷款,养了第二批鸡,这次挣了几万元。但第三批时,新冠肺炎疫情来了。2020年2月,鸡蛋一摞摞堆在仓库,越积越多。一天夜里,“轰”的一声传来,新捡的一批鸡蛋倒落,碎了一地。
哑巴陪他连夜收拾。那几个月,哑巴负责喂鸡、捡蛋、装箱,陈小峰在外送货。这一批蛋鸡,又亏了。
陈小峰养殖蛋鸡,“三批亏了两批”的事情,跟当年他“带回个哑巴”一样,周边人都知道。即便如此,一些商贩仍愿意赊鸡苗、饲料给他。
这不是陈小峰第一次创业。在母亲眼里,儿子“是个苦命人”。
他上初中时,一次家里拿不出学费,姨父送来钱救急。想着自己学习不好、家里还有个小他一岁的弟弟,他作了决定:不上学了。
退学后,他购进一批文具,在村里的小学门口摆摊。有的学生钱不够,就赊给他们。有的迟迟不还钱,他也不忍心讨要,“那时候的农村娃娃,有的连中午饭都吃不饱”,账款于是不了了之。他第一次“做生意”,以失败告终。
3
薛集镇地处鄂豫交界,东面和北面与河南接壤,是“一脚跨两省”之地。这个人又是从哪个方向来的呢?
一次,陈丰举的孙女在家拼装中国地图,正好哑巴到他家串门,陈丰举让他指认自己是哪儿人,哑巴指向贵州。陈小峰跑去派出所请民警查询,仍旧没查到。
陈小峰为哑巴寻亲的想法,一直没有中断。他解释说,“并不是想让哑巴走”,只是想着他一个聋哑人,独自在外这么久了,肯定也有想家的时候,“家人肯定也念着他呢”。
几年里寻亲无望,陈小峰和妻子商量,给哑巴办个身份证,户口就挂靠在他们家。他们去派出所,没能办成——这是一个暂时失去了合法身份的人。
但从这家人的心理上,哑巴已经在家里“落户”了。他们逢年过节会带他一起走亲戚。陈小峰有时临时在外吃饭,都会打包一份,带回家给哑巴。哑巴把零花钱用来理发,不会乱花。过年了碰上拜年的小孩,他拿来发压岁钱。
孙金莲有时去镇上赶集,会给哑巴带双鞋。哑巴身高1.73米左右,比陈氏父子高出不少,鞋子穿43码,是“全家脚最大的”。
在家里,哑巴喜欢看战争题材的电视剧,陈小峰也一样。起初,陈小峰没钱买电视。农村的夜晚没什么娱乐活动,他俩有时去邻居家看电视。时间久了,陈小峰担心打扰别人。2016年,他买了一台,安装在养鸡场的“客厅”。他认为“哑巴很聪明”,因为教他用遥控器操控电视,“只教了两遍,就学会了”。
哑巴后来也表现得对回家没什么信心了。养鸡场旁种着几棵大树,他跟村民们开玩笑,指指树又指指荒地,意思是以后自己死了,就麻烦大家砍下这几棵树做棺材,他就“永远躺这里”了。
也有闹矛盾的时候。
哑巴爱喝酒,一天两顿。一个夏夜,他在外喝多了酒,边走边挥舞空酒瓶,还敲别人家门。不少人家被吵醒了,第二天一早来找陈小峰说理。陈小峰有些生气,比划着警告他以后不许这样了。到了午饭时间,他不见了。
陈小峰和父母出门寻找,直到第三天才在邻村一户人家找到。他独自蹲在别人屋檐下,看到陈小峰,还不理睬。陈小峰又好气又好笑,拍拍他的胸脯,又拍拍自己的,意思是“我的心你还不懂吗”。哑巴跟他回了家。
这次,陈小峰想了个办法:他找出废旧包装盒,裁下小块硬纸板,用黑色签字笔写下自己的地址、手机号,再用透明胶带一层层缠得严实“防水”,放进哑巴的衣服口袋。以后如果走丢了,就拿给别人看。
担心联系牌遗失,陈小峰一共做了6个备用。
4
2020年冬天,湖北省推行“一村一辅警”,薛集派出所到陈庙村调研,在村委会与村民们推荐下,陈小峰当了辅警。村里有精神病人13人、孤寡老人10人,都是他重点走访的对象。当上驻村辅警,陈小峰接触到了更多警务知识。
2021年11月初,村民们开始接种第三针新冠肺炎疫苗。苦于没有身份证,哑巴一针也没打上。陈小峰再次动起了给他寻亲的念头。
几年里,民警通过人像比对等手段,多次为他查询身份信息。一次,查询到四川省有一个男子身份信息与其相似度高达97%,打去电话询问,家人称“人在家好好的,没走丢”。2021年9月,民警查询到另一个人的身份信息与他相似度较高,继续查询,结果显示对方已接种过新冠肺炎疫苗,显然并不符合。
这一次,民警带上哑巴来到老河口市特殊教育学校,希望手语教师能够帮上忙。
但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手语教育,手语老师也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看来又没有太大希望了。突然,他拿过一张纸,试图在纸上写字。在民警与手语老师帮助下,纸上先是出现了歪歪扭扭的“都”“江”二字,随后,他又在“都”和“江”中间画出两个上下连在一起的半圆,疑似绞丝旁。
会不会是人名?在当地,“都”姓并不多见。户籍民警周馨根据经验推测,绞丝旁的字中,用于人名较多的是“红”。民警们以“都红江”为关键词,通过公安部门户籍信息系统查询,显示全国叫这一名字的有9人,分布在黑龙江齐齐哈尔、浙江绍兴、河南滑县等地。逐个比对,最终发现河北泊头市的一名人员信息与其高度相似。
老河口警方联系上泊头警方,请求核实。恰好,泊头市四营派出所民警苏晨辉对一位叫都红江的走失村民情况有所了解:都红江1968年出生,2008年走失,走失前,其父母已去世,家中还有姐姐妹妹。
亲人中,最早通过警方得知都红江“有可能找到了”的,是都红江二姐的儿子穆海明。
苏晨辉发来湖北警方传送的视频与照片,穆海明一眼认出这是舅舅,“模样变化不大,就是稍微苍老了些”。穆海明当即给大姨、三姨、小姨每家打了电话,通报“这一特大喜讯”。据他回忆,电话里“每个人都哽咽了,吵着要马上动身,立即去湖北认亲”。
这天是周五,两边警方合议,慎重起见,再做些核实工作。等到周一,双方再通过视频连线,确认后就办理认亲。
都红江的亲人早已“炸开了锅”。挂完电话,大家迅速分工:大姐都英平、二姐都英随、三姐都英兰、小妹都英敬去四营派出所,配合警方进一步核实。6个外甥、1个外甥女,一拨儿去定做锦旗、到时带给湖北警方,同时给“恩人”准备特产;另一拨儿上街去给舅舅买新衣新鞋。各家选定代表,准备周一视频认亲完毕,即刻出发前去接人。
他们准备的心意,是几箱牛奶和泊头特产的“十里香”白酒。
都红江的外甥都春辉在郑州工作,接到消息后,反复跟妈妈确认。母亲告诉他,看了照片,“千真万确”。这个25岁的年轻人当即向公司请假,准备周一从郑州开车,与表哥们在高速路口会合,一同去接舅舅回家。
11月13日和14日这两天,对都家人来说,兴奋又漫长。他们期待着,周一上午的视频连线早一点到来。
5
13年来,都红江的失踪,一直是全家人心中的痛。
都红江天生聋哑,没能上学,也没成家。父母相继去世后,他住在父母留下的房子里,大姐、三姐就嫁在本村,离得不远。2008年10月4日那天晚上,都红江没回家,家人以为姑妈留他住一晚。第二天,他还是没着家,一问,姑妈根本没见着他。一家人这才慌了。
全家人除了上学的孩子,全部请了假不上班、放下地里的活儿,分头到周边寻找。全村在家的村民也自发出动寻人。
都春辉记得,那年他12岁,“上百号人找遍附近百十里地,连续找了大半个月”。
家人找到市里的电视台、报社打出寻人广告,在周边张贴寻人启事,没有消息。
他们想过最坏的结果。有一段时间,全家人特别留意、甚至害怕电视或网络上播报的车祸消息。有一次,新闻里说吉林省有一辆卡车撞了人、寻找受害者亲属,听那外形描述“特像咱舅”。几个外甥找到这条新闻,回放画面,一帧帧比对,确认不是舅舅,才稍微松下口气。
有时,在外看到流浪汉,都家人都会上前仔细看看。有流浪汉流落到村里,这家人也会给对方盛饭盛菜,照料一阵,同时把都红江的身份证照片拿给他们看,询问是否遇到过。
这张证件照,是都红江走失前不久照的。姐姐和妹妹担心他不能说话,在外受罪,常常对着照片抹泪,自责没有照顾好他。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四姐妹去算卦。算命先生告诉她们,“等着吧,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
最近几年,家人们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过寻人信息,依旧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一年又一年过去,舅舅还是没回来。”都春辉说。小时候,爸妈农忙,他是舅舅帮着带大的。他总忘不了,舅舅给他做饭吃,舅舅带他去小卖部买零食,舅舅牵着他、抱着他。
每到过年,乃至平常日子里的家族聚餐,大家都会给都红江盛一碗饺子,留好座位。穆海明说,可能每个人都预想过最坏的结果,但又都留有一丝希望。
走失前,都红江在村里“口碑不错”。他爱给人帮忙,别人会的,他也会,犁地、割麦、砌砖、盖房,样样干。外甥们说,舅舅在家时,为了谋生,跟人学习了盖房的手艺——这足以解释,当他流落到湖北,可以很熟练地帮人家盖房。
在都李泊洛村,都家是大姓,10多年来,年轻人外出务工,年底回到家也会牵挂,他们会问的一个问题是,“哑巴叔回来了吗?”
6
得知这次“极有可能”帮哑巴找到亲人了,陈小峰“一时间心情有些复杂”,替他开心,又舍不得。
他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比划给哑巴,“但他好像没听懂”。晚上,他们照例一起吃饭、看电视。
11月15日一早,天气晴好,薛集派出所民警来到陈小峰的养鸡场门口,与四营派出所民警进行视频连线。隔着屏幕,起初,都红江有些茫然,当镜头拉近,看到那边的姐姐、妹妹和外甥,他“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双手枕在额前哇哇大哭,随后对着镜头连连招手、边拍打着自己胸脯,使劲点头,嘴里不断发出“巴巴”的声音。
这是陈小峰“第一次见哑巴哭”。也是第一次知道,他收留了12年的哑巴,名叫都红江,河北泊头人,出生于1968年,比他大14岁。
镜头那边,都红江的亲人也哭成泪人。他们决定立即动身。穆海明开一辆车,带上3个表兄弟和小姨,从四营镇出发。都春辉算好时间,当天下午从郑州驾车出发。
这天下午,陈小峰看到,都红江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难掩激动。晚饭时,都红江比划着告诉他,自己“舍不得”陈小峰。
第二天,两人不约而同提前半小时起床了。都红江跟往常一样,清理鸡舍,给鸡喂食,又打扫了院子,围着养鸡场转了好几圈。半个月前,陈小峰养在养鸡场的狗下了崽,眼看天气一天天冷起来,都红江找出一件旧衣服,在厨房角落做了个狗窝,再把狗崽子们一只只抱进窝里。
10时30分许,在老河口警方带领下,两台河北牌照的小车驶进养鸡场。一下车,看到哥哥,头发也已泛白的妹妹哭着跑向哥哥,都红江先跪倒在地。外甥们也哭了。
陈小峰眼圈红了。
见完哥哥,都英敬转身看到陈小峰,此前,他们在视频里“见过面”。都英敬双腿跪下,拉着陈小峰的手哭着连声说“谢谢,谢谢大恩人”。外甥们跟着跪了一片。陈小峰单膝跪地,连忙扶他们起身。
外甥们手忙脚乱帮舅舅换上新衣、新鞋。都红江一早就收拾了行李——陈小峰买给他的衣服装进一个纸箱,还有过年时的一双新鞋,他只穿过一次。
中午,都英敬提出,请陈小峰一家和周边邻居一起去镇上餐馆吃饭。陈小峰建议“整点酒”,都红江给他、给每个人敬了酒。饭后,都英敬结账时发现,陈小峰已跟老板打好招呼,把账结了。
下午两点左右,一家人准备出发。陈小峰给都红江准备了两条烟——是他刚来时,最爱抽、只抽过几次的那种“好烟”,一个新保温杯。
保温杯里泡好了他平常喝的绿茶。都红江没用过保温杯,陈小峰手把手教他,提醒“喝之前不要被烫到”。
陈小峰的父母,还有附近抱着孩子的村民、提着竹篓的妇女、穿着棉袄的老人,都来道别。人们边笑边抹眼泪,挨个跟这个一直不知道身份的人郑重握手。他们放慢语速,用老河口方言告诉都红江的家人,“得空了再回来玩”。
都红江上车了,陈小峰上前一步,从兜里掏出1000元钱,塞向他的口袋。家人推辞,小峰说“一点心意,回去买点烟抽”。
车门关了,发动机响起,都红江示意外甥等一下。他打开车门下车,跪在地上,郑重给陈小峰磕头。陈小峰赶紧扶起,拍拍他的肩,右手比划了几个动作。都红江点了点头。
7
都红江回家时,又是一个雾天。
这次又是全村震动,只不过,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喜悦。
11月17日清晨,外甥们连夜开了10多个小时车后,把他带到了村口。
村民们敲锣打鼓迎接,路边两棵老树牵起红色的横幅:“欢迎都红江回家”。鞭炮噼啪作响,串串白烟融进雾色里。
亲人们抱着他搀扶在一起,痛哭不已。在家人与乡邻们包围下,他们彼此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又一遍。
都红江没有上过学,亲人们只能在他的手势中连蒙带猜,大致知道:2008年10月4日那天雾很大,他去姑妈家路上不知怎么喝了些酒,继续赶路时酒劲儿上头,倒在路边睡了一觉。醒来后,雾还是很大,他迷了路。
他是怎样流浪了一年,出现在老河口,仍然没有人知道。
都红江走后,陈小峰有点不习惯了。十几天过后,在养鸡场里,都红江的房间里还保持原样,他没能带走的衣物洗净晾干了放在床铺上,牙缸搁在一台旧冰箱上,没喝完的半壶自酿葡萄酒立在墙角。
煮面条时,陈小峰会习惯性地多下一点,放进锅里才想起那个“哑巴”已经回去了。
每隔一两天,陈小峰会和穆海明视频连线一次。穆海明告诉他,舅舅回去后,全家先是摆流水席,请全村人吃饭庆祝;而后,全村人又挨家挨户接舅舅吃饭。舅舅有了新户口本,低保和残疾证手续也在办理中,村里还准备为舅舅维修房子。
陈小峰对记者说,他虽然很想念都红江,但从没有主动联系过穆海明,“咱不能打扰他的生活,但又盼着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
为防止都红江再次走丢,家人给他买了部手机,教他只要手机震动就赶紧回家。他很聪明,学了两次就会了。这一点,陈小峰是经记者转述得知的。
得知此事后,他沉默几秒,第一句话是“他们怎么没告诉我”,像是错过了什么重大消息。他随后说,“要多教教他,以前我给他备过对讲机,他喜欢乱按。”
都红江回家后,衣服口袋里仍带着陈小峰做给他的联络牌。“仅从这点,就能知道小峰叔把我舅照料得多好。”穆海明感慨。
只有陈小峰和都红江才明白,临别时,他们所打的一个手势是什么意思。严格来说,那是个“秘密”。那天上午,亲人们还没赶到,做完手头所有能做的活儿,哑巴将养鸡场钥匙交到陈小峰手上。陈小峰示意他“放到老位置”。告别时,他右手的手势,意思是,“回去后,想这边了随时回来,自己拿钥匙开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房家梁】标签:

加快场景创新 科技部首批支持建设十个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
2022-0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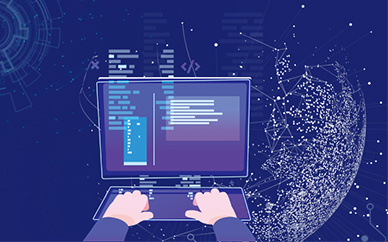
科技部公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方案》 亮出10项行动内容
2022-08-16

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冷链行业市场规模正在快速膨胀
2022-03-21

行业正站在风口 数字化时代在为传统的自行车产业赋能
2022-03-21

以做强实体经济支撑为重点 成都单个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同比提升
2022-03-21

拥有多个国际赛事的直播版权 广州游戏电竞企业业绩向好
2022-03-21

投诉量激增 直播带货存在这么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022-03-21

工作专班深入到各企业 春寒料峭挡不住松原市施工热情
2022-03-21

引导企业向提供“产品+服务”转变 湖南加快智能农机服务化转型
2022-03-21

创新平台建设和科技成果转化 德州加大力度重奖创新
2022-03-21
科技部公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方案》 亮出10项行动内容
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冷链行业市场规模正在快速膨胀
行业正站在风口 数字化时代在为传统的自行车产业赋能
以做强实体经济支撑为重点 成都单个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同比提升
拥有多个国际赛事的直播版权 广州游戏电竞企业业绩向好
投诉量激增 直播带货存在这么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工作专班深入到各企业 春寒料峭挡不住松原市施工热情
引导企业向提供“产品+服务”转变 湖南加快智能农机服务化转型
创新平台建设和科技成果转化 德州加大力度重奖创新
潜在风险进一步放大 商品房现房销售已是大势所趋
有序复工复产 1—2月份工业经济发展新动能持续增强
多层次高频调度 1至2月河北省工业运行先行指标稳中有增
以车路协同为基础 智能交通推动城市交通绿色高质量发展
人才短板成为制约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
通过技术手段整合调配供给资源 家政行业不断提质扩容
强化产业链深层次合作 加强重大装备国产化“一条龙”模式构建
如何进一步提升纳税人缴费人的减税降费获得感?
探索建设大数据及网络安全示范试点城市有哪些积极意义?
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实施缓缴税费政策有哪些积极意义?
进一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消费者需注意辨别谨慎消费
将“走出去”变“请进来” 西安贸易产业转移承接作用不断得到增强
厦门应如何融入“数字中国”的重大战略发展大局?
江苏省如何不断满足老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建设一体化的职业健康信息管理平台 天津职业人群保障加强
潜力持续释放 1—2月乡村消费品市场恢复略好于城镇
直接对接社会化服务 楼宇调解室将整体提升青岛劳动争议水平
成功化解纠纷11.47万件 银保监会服务质量日趋提高
春雷响百虫出 惊蛰文化在其他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
青绿山水画在古代山水画发展史上有着怎样的影响与地位?


- 开播即爆款 “文化类节目收视率低”这一固有印象被推翻
- 涵盖了109件真迹作品 凯斯·哈林展览将持续至6月13日
- 带有一点自信的自嘲 “隔路”是另一种味道的“凡尔赛”
- 与文渊阁前后呼应 “何以中国”特展隆重致敬文化大成
- 严重者可造成暂时性失明 享受冰雪运动要注意眼睛的健康防护
- 种类繁多让人眼花缭乱 选购牛奶时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 网课让孩子感到不安焦虑怎么办?八问八答回应广大家长关切
- 循环系统很容易受到刺激 “倒春寒”期间老人该如何做?
- 青少年患者睡眠问题日趋增加 9条建议为孩子助眠
- 我国肥胖人群正逐年递增 不良饮食习惯是重要诱因
- 如何减少噪声对听力的损伤?这份耳部和听力保健小贴士请收好
- 强化住房限购措施 西安限购限售范围进一步扩大
- 多种方式增加供给 进一步降低新市民和青年人的居住成本
- 预计9月下旬海口可实现安居房申请网上办理
- 政策调控力度持续升级 8月百城二手房市场均价止涨转跌
- 8月中国新房找房热度依然保持平稳 环比微涨0.2%
- 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销售价格备案管理 今年全国楼市调控刷新历史纪录
- 西安第二批集中供地中28宗为现场拍卖方式出让
- 细分化需求得到释放 房屋居住的属性越发凸显
- 佛山顺德龙江近日挂牌商住地起拍价约19.88亿元
- 青岛市4宗地竞品质抽签结果出炉 地溢价均约15%
- 坚持政策支持、多方参与 浙江版保障性租赁住房明确新增比例目标
- 简化审批流程 武汉将实现房源申请配租全程网上办
- 哈尔滨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例 活动轨迹公布
- 哈尔滨市公布3例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活动轨迹
- 山东深耕文化资源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 今年新增952件(套)!南京大屠杀再添新证
- 四川非遗传承人张雄志:巧手捏面塑 指尖传非遗
- 10月以来我国寒潮为何如此频繁?中国气象局回应
- 56位残疾人士登上黄山 互利互勉共建生活希望
- 安徽潜山两车相撞 已致8人死亡3人受伤
- 上海洋山海关首次在出口货运渠道查获夹带卷烟
- 山西忻州古城:一城风华延续千年历史文脉
- 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右旗公布1例无症状感染者行动轨迹
- 新增“53+1” 内蒙古累计本土确诊病例增至185例
- 昆明公安打击破坏生物多样性犯罪 抓获130名涉案嫌疑人
- 山西朔州“11·11”较大透水事故调查报告发布 对38人问责处理
- “海关国门小卫士”竞争上岗 淘汰率接近一半
- 深圳摧毁特大品牌化妆品走私网
- 28人被问责!山西石港煤业“3·25”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 湖南韶山以河长制带动全民治水 让每一处水面“长治久清”
- 上海市奉贤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袁晓林被“双开”
- 民进会员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心怀大我 敢讲实情
- 80岁“留守”奶奶短视频诉孤独 千万网友心疼:我们陪您唠嗑
- 40年来为子弟兵送出1.3万余双布鞋和鞋垫的“布鞋奶奶”走了
- 当男幼师是什么体验?他们说:有委屈尴尬 但大部分是幸福
- 庐阳警方通报幼童坠亡事件:嫌疑人已被刑拘
- 内蒙古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
- 哈尔滨市启动部分地区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 四川通江发生两车相撞事故 致3人死亡




